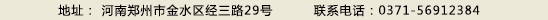方向一
自白庙至栗城约六十里,于某而言,此乃长途,盖因某有晕车之症。
某晕车始于商丘。是时,某八岁,得病,全身抽搐不止,貌如转筋。某家中满客,皆为观病。某口目抽搐,难以视物,唯觉死之将近。父蹲一角,泪落如雨。叔曰:哭何,可治。次日,某与父母登车北上,前往商丘。
天尚朦胧,冬寒正紧,某等三人踏入客车,向前行去。途中,某数次抽搐,难以言语。偶醒之际,忽觉胸腹燥热翻滚,耳浑头昏。父道晕车,只需睡去便可。
某静静睡去,朦胧中时昏时明,时抽时吐,终于挨到商丘。行走走久,至一户非亲之亲。及院时,又抽数次,某已然麻木。
数日后,治疗。须打吊针。某心甚惧,母道,无他,不痛。打针之时,某平静异常,呆望针尖刺入手背半寸长,心有异样。吊水滴答下落,宛如泪珠。闲时,某随父母外出,此时,某不想方向,只知随其左右。至一桥,见有卖玉观音者一,某观望良久,父买二,一某,一吾妹。某戴其于颈,意态畅然。
回家之时,已在两月后,某于车上,头目昏然,遍吐狼籍。及至家,已恹恹将崩矣。向西而走,至家。自此八年几不坐车。
八年后,某上高中,前往栗城。此时,某晕车之症又重,坐于车上,用书包紧贴胸腹,以减震荡,而头晕依旧。某于友尽道其苦。友却恰恰相反,反倒乐此不疲,无事便东南西北,不知其处。
某每逢假期,不得不抱腹吃药,郁郁而归。某不记车坐几次,头晕几回。只记一日上午,适值周末,某沿学校慢慢回走,从早至晚,整整一日,终于到家。某双腿如注铅,隐胀隐痛,而某畅快非凡。某不必担心晕车之症,不必忍受颠沛之苦。
王某问在下,奈何走六十里家去。某道:此时不做,更待何时。王不信,其总道某如此自虐乃因他故。某不然。就人而论,某既无权定人之矩,亦无力阻人之口。纵然如何,也无他法。王不语,某无声。书曰如此,书曰如此。某就书论事,就事论文,不通。某不论事,不论文,不行。某读大悲神咒不得脱,诵金刚佛经不得空。日益孤苦,难以自拔。庄子有文,某日日诵之,司马有史,某时时读之,自此常讲佛论道,攻诗著文。旁人观之,常自窃笑,指某曰:变态。
某岂有不知,常扪心自问,某读经乃为境,读藏乃为道,读史乃为智,读诗乃为志。奈何吾欲遂己之志,而彼等尽撩拨也哉?
日随时去,名筑言起。平平十二班,无人不知某变态;全班百多人,都道在下是畸胎。
金秋苦菊,已被孤立;寒冬霜雪,独伴梅花。王某与在下善,人称二王。一日,有女李氏指某笑曰:二王者,二变态也。某泪如泉涌,莫能仰视,坐不举目,走难抬头。至宿舍无人之际,独吊于门框之上,嘶喉高歌。每于月末,悄然回宿舍,独走于无人大街,当六十里如一步。
一日回家,遇王某,邀某作客。转至其外祖家,已近夜。晚饭毕,走至田间,散步良久,抽烟数枝。是夜星光寥寥,弦月莹莹。景其清清,境何淡淡。
如此之星空,一则某乡有,另一则便在张庄闸。王与某曾步走向北,遇一河,随行三十里,欲求其源而不得。见一坝立其上,大书“张庄闸”三字。其水清且缓、净而远,向北延至碧田高处。一白发迎面而来,指某曰:是为学生否?南校否?吾有孙在彼,不知何时归?某愕愕不知所答。西行而去,两髦耋坐桥头,其一曰:狗凳子还在否?答曰:尚在。曰:吾闻东庄老虎已死,不知其真假。答曰:然,旧友皆已尽,吾等不远矣。随即默然,呆坐抽烟。王与某转至小路,有树两排,葱葱郁郁,罗列左右。某于草中捡五彩雉鸡尾一只,埋一树下,并许下三番誓愿,暗付他日扬名之际,定取此物。辗转回校时,夜色渐近,有星数颗棋布高天之上,一弯弦月轻诉月光微曲,某论李青莲明月出天山句,皓然神思,悠然向往。
此后一月,高考已毕,某归家中,永别张庄闸!
此时路渐平荡,车多安稳。某忽念一年前至孙庄会友,某逢酒必饮,有劝辄尽,是故大醉。吐数次,晕尽然。歇至傍晚,某拖车独去,加车全速,于路高呼,傍若无人。窃思倘或失手,某当轰然崩倒,纵不死透,亦难脱生。于是手渐松,目渐闭,车嘤嘤而行,某不知其所往。正欲放手,忽闻有人相唤,声似吾母。某警而醒,既而双目浸润,口鼻哑然,双手骤然紧握,缓缓而行,渐至家中。
高考后两月余,将至开封求学。某与开封,相隔约四百里,其途虽较栗城远甚,而某较之当日亦相隔多矣。某离家时,母亲曰:开封与家数百,纵尔欲步,奈何天高地远,非数月难及。某笑曰:关公刮骨疗毒,其痛难当,是故喝酒吃肉不言不语。母亲不答。某自思,高中小子,灵智不开,及心痛则以肉痛医,及肉痛又以他痛医。是故关公不道,其心早溃。周郎箭愈,尔疮又发。而某自高中来,日日精进,时时煅造,已近百痛不侵之体,岂会独奔四百里以求解脱也哉。
既行,来至开封,友共十人,其态各异,父指某铺曰:近窗固好,奈何北风紧。某自迟疑,近窗固然,却为西窗,何来北风袭紧之说。翌日父去,某与众人近校闲走。友曰:东西甚善,南北不足。某否然,依某观之,南北乃通天大道,东西却微丈胡同,自然南北善而东西鄙。友尽非然。某不语,见高日悬东天,烈火炎炎。某问几时,答曰正午。某轰轰然煞时立住,举目观日,赫赫居于正东,又问几时,答正午。某长叹指日道:此乃南也。众皆亦然。某苦笑曰:在下以为东也。众哂笑。乃知吾有迷向之症。
归舍,方知父亲北风袭紧之说。
进校军训,问何处集合。曰:东北球场。某至东北处,见一石立其上,上有“明德”二字,其后乃水泉也。某遍视良久,不见球场,苦思几何,方悟此地乃正南也。扬首他顾,竟不知何为东北。某木木然不知所归,独立于广场之上,周无所见。后舍友至,指其去处,某方与彼同道而行。及到处,心愣愣依旧。晚回教室,学长找人歌,全班无人出列。某叹气而出,至讲台昂首闭目,高唱两只老虎。举班哗然,数众窃笑不止。某叉手立其上,无动于衷。某自高中时,受尽嘲弄,尝遍热讽,岂在乎此小儿也?彼等皆笑我痴,岂知某笑彼等愚哉!
日已昏昏,某独归寓,见一狗男女互搂于市,相啃于街。后有卖臭豆腐者扬其幡,状如老粪,味似鲜屎。某遮鼻而过。有一老妇乞余,某忽念一年前自王某外祖家归,道行至街,一老汉随后而出,某于路捡硬币一枚。老汉尾随某数丈,忽道:吾失钱一元,被汝拾去。某哑然失笑,交其手。彼面目转红,颤手取去。彼乃诈,非为乞。及某坦然相与,彼反为乞者。某自坦然,彼却失然。今日观老妇乞者,不知其乞其诈也。
近某言曰:吾本良人,误入他乡,乞钱归家。某遍翻口袋,仅有十元,道:某钱只够一饭。妇曰:吾女价非一饭。言毕,一少女窈窕者从后而出。某愕然不知所答。妇曰:久无归所,乞处一宿。某曰:吾识女子数人,或可一宿。妇扬眉道:汝何人哉?某道:开大新生。妇冷笑而走,少女铅坠细步,挪移而去。某浑然不知所遇。后方知其既非乞亦非诈,乃为娼也。
次日军训,倾目听令。所喜军令只讲左右,不讲南北。某自边卒而至领队,自泛泛而至标兵。一日,领队而出,自左线带至右线,来往数次,间不容歇,某忽胸腹翻滚,耳目鼓胀。某诧异非常,乃知晕车之症又重,难以自持也。是时,队形渐乱,轨迹渐无。教练大呼领队,某快步而出。教练劈头乱骂,高叫白痴。某冷眼相对,放声道:某非白痴。教练豁然一惊,道:既非白痴,奈何队乱。某道:阵乱责在将军。彼大怒,带某至观台后,尚未言语,赵导慌然赶至。问清缘由,讲明事故。赵曰:责在教练,可致歉。某否然。赵不解。某曰:某已不愿军训,道谦亦无益。赵曰:教练已应致谦,汝当大度。某笑曰:可使某扬言詈骂而默然致歉乎?赵导忿然不快。某道:某之脾性,自高中已然变了,宁折勿弯、宁碎勿全!二人默默而走。某独坐地,自午后至傍晚,见浮云往来摇走。
晚择标兵,某等列入方阵,别行苦训。正踢方步,右脚进一石粒,初无异状,百步之后渐成痈泡。取石后,剜泡掘痈,挤脓撕皮,其痛似刀剜剑刺、斧砍戟刹。每踏步宛似猛踢刀尖。某口呼军号,脚踏脓血,忍痛抬踢,畅爽已极。
军训毕,始课,每逢课余,众皆东南西北,满城游荡。某独立于天台,极目眺望,西观金明池,东望繁荣景,人声隐隐如远雷,遥遥渐近。
及众人归,皆道包公湖鼓楼街。某无限神往,友指其南北,某苦思良久不知其所,反问数遍亦不得其位。友指其车路,某暗暗铭记。一日,某独登公交,欣然东去,未至两站,肠胃已近沸腾矣。某无语,悄然下车,沿站牌步行,走无数站,已失其处。转至一侧,问一老者某处,指余曰南。某欲行,不知何为南,回身问其南北,答曰左。
某转左,行数时,见其地偏远,不类某处。翻身看表,日已十一时,近午矣,抬头再走,猛见日头悬于左空,方知刚走之路,为西非为南。某不知其所,腹又饥渴,问一妇此地何处,距城几何。答曰某庄,离城十里。某苦笑无语,见一车驶来,上有至某站,不得已而登。强忍呕吐半时,至于某站,恍惚见故道,欣然下车,识其归路,徒步而行矣。
晚,宿于七楼天台。是夜星光璀璨,明月皎皎。某尽去衣衫,铺席横卧。时有微风抚体,颇感清慰。偶念军训篝火会时,数十人交手相围,绕圈而嬉。某左手处乃一女,手矜矜不出,貌似贞持。某微微冷笑。某自十岁诵吟唐诗三百,十四岁读基督圣经,十六岁研佛门禅宗之道,十七岁求道藏真言,虽无所成,亦自许空空不滞于物。彼猴臀猪脸,尚在某前做惺惺态也。
悄然松手,默默回行,见数女爹爹肉态,扭腰撒娇,教官嘿嗨卖弄,彼此妖娆。二女俨然家主,遥遥指某道:新生,何故傲慢,不叫吾等学姐?某静默而过,态似不知。女曰:何无礼也!某讪讪而归。至南门处,恍惚又当其为东门。
某高中时,其门与开大似,而门向东,是故见开大南门自为东门。某故乡有东南西北四干道,某之方向便立于此。及至开封,却以东西为南北,以南北作东西,其位之错乱,非止一端。某校至大梁门,乃自西向东也,某尝以为自南向北。某在闻莺阁时,日西斜至其处,天明方归。晚宿茶阁内,以为守夜。常过大梁门,约计五里。闻莺阁有房十数间,独占层楼,其地颇广,某独宿于此。
初,闻楼内嗡嗡有声,某不知何故,心慌慌然,观寻良久,方知排扇故也。转至榻房,卧床静思,有鼠吱吱鸣叫,活动于天板夹层。其一窜至屋内,来往觅食。某观其半夜,熄灯就寝。
后夜,李某至,于房内观球。二队刚接,便进一球。某等大喜,持手机发短信至电台,以资鼓励。短信发毕,二队至终竟不进。某二人唉声叹气,怏怏不乐。
宿时,因恐风大,特闭南窗。次日天明,赫然见窗大开,阴风袭袭。馆居二楼,其外有铁窗围护,非从内不得开。然楼内人早尽散,只某二者。彼此相对,皆不知窗如何得开。苦思良久,不知其法。某忽记七岁时,与北街段某数人,至南处清凉山挖蚌壳,于路见赤蛇交于地,某等绕道而行,至清凉山,见一物似黑犬黑狐者箕坐于地,长舌吐出,瞪目视某。某惊而相问,皆道无所见。某惧而奔回,不足里许,被数人寻回。辗转又至,已无物矣。某挖贝数许,又见数骨,怖而走,归家,心惶惶不定,数日方安。某至今不知所见何物,亦如至今不明窗何为开也。
后至茶楼,某持张某所赠金刚经、王某所赠护身符。舍友知此,故意妄为,每逢闲暇之际,约集数人,看《午夜凶灵》、《笔仙》,某懦懦不敢近。众皆笑。
某夜宿茶楼,来往不便,多迟到。有教员许某冠院长者集会,某在此列。许曰:班本阴盛,若众皆不起,则阳愈衰也。
某嘿然冷笑,悄声道:夫智士不合于众,英雄不流于俗,沧海横流,方显本色。如班内数女哗然躁躁者,不过跳梁小丑尔。且夫真龙必藏,猛虎先卧。若此张牙舞爪者,尽为劣豚苍狗。
有女马氏甚不忿,瞥视某良久。某无视其状,依某观之,此女苍狗定矣。
既出,某至茶楼,辞工,后回,女主扣工资三十,某不喜而归。见女某氏,忽记昔日相知之事,已愈年矣。某遮颜而过,貌似不识。
是时寒冬大雪,尽铺于地。有师使生讲课,正值某也。某手不持稿,目不观书,独登讲台之上,欲诉新悟之天地人三道事。正欲开口,赫然见旧好下坐一旁。某神思逸飞,心生旁鹜,若有所思,讲李杜王三诗毕,默然回位,离班而走。
夜宿寓,诸君面目严严,正轰轰烈烈闹种菜收菜之革命也。某偶见聂某网号烁烁,正与某女余氏聊天也。某忽记数日前某事,其相识固然奇特,其相往亦多怪谈,及至各奔前程者,又缘相隔半千,难相见也。当知人心千万,难求定者。
后乃分道扬镳,自此七年不曾见!
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治得好全国白癜风十佳医院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hedasoft.net/kjcp/1661.html